四月是受难与复活节,我们鼓励读者本月读完整卷马太福音,每天以祷读方式灵修,默想其中一节,将经文化成祷告和行动。
本月祷读资料由夏超凡牧师撰写,特此致谢。

梅干,是许多人对日本文化的味觉印象。
当梅干轻轻落在舌尖,强烈的咸味瞬间冲击味蕾,咸味渐渐退却后,酸味隐隐浮现,令人不禁皱起眉头。咸与酸之间,一丝澹澹的甜味悄然而至。
品味梅干,彷彿在细尝日本社会的百种滋味。那片浓烈的集体意识扑面而来,随之浮现的是日本人在巨大齿轮下的生活辛酸,以及深藏于社会隙缝中甘甜细腻的人情味。开始为日本祷告前,我们怀着尊重的心,先来一颗梅干吧!


梅干,是许多人对日本文化的味觉印象。
当梅干轻轻落在舌尖,强烈的咸味瞬间冲击味蕾,咸味渐渐退却后,酸味隐隐浮现,令人不禁皱起眉头。咸与酸之间,一丝澹澹的甜味悄然而至。
品味梅干,彷彿在细尝日本社会的百种滋味。那片浓烈的集体意识扑面而来,随之浮现的是日本人在巨大齿轮下的生活辛酸,以及深藏于社会隙缝中甘甜细腻的人情味。开始为日本祷告前,我们怀着尊重的心,先来一颗梅干吧!

日本贫困危机观察
中年人的贫困
这群人是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毕业的大学生,俗称「就业冰河期一代」。由于日本企业偏好社会新鲜人,他们错过了入职最佳时机。如今已至中年,仍是打工族或派遣员工。健康状况像个定时炸弹,一旦爆炸,就会跌入无底深渊。
英国社会学家提出多项衡量「相对贫困」的指标,例如是否有能力购买家电、负担教育费用、偶尔外出用餐、维持基本社交生活等。一般而言,当收入低于该国平均收入时,即属于「相对贫困」。
「绝对贫困」是指无法满足生活基本需求,包括收入低、营养不良、健康状况恶劣及无法接受教育等。
浮世绘与印象派画廊
喜多川歌麿、葛饰北斋和歌川广重被誉为「浮世绘三杰」,是日本艺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喜多川歌麿笔下的美人,一颦一笑皆灵动传神;葛饰北斋与歌川广重的风景花鸟画作,犹如一张张旅行明信片,以独特的视角捕捉江户时代的名胜风光。这3位大师的作品不仅在日本本土备受推崇,更主导了西方世界对浮世绘的理解。
文艺复兴以来,西画追求呈现三维空间、色彩与形态的和谐。日本浮世绘的出现,像一记重锤撼动了这个传统。浮世绘以平面色块的涂染技法、二维的画面处理,以及大胆的不对称构图,启发了一群西方画家摆脱写实主义的束缚,转而探索抽象的表现手法,促成印象派与后印象派的诞生。
▲ 喜多川歌麿
《当时三美人》是美人绘大师喜多川歌麿的经典之作。眼角的温柔、秀丽的鼻梁……画家细腻刻画了江户时代最负盛名的3位美人,将她们各自的神韵拿捏入微,充分展现了这位美人绘大师炉火纯青的画工。
▲ 爱德华 • 马内
平涂色彩是浮世绘的一大特徵,此绘画技法最早被法国印象派画家马内应用。《吹笛子的少年》中,马内将人物置于单调的平涂背景前,刻意澹化传统西画的立体空间感,捨弃明暗阴影与视平线的表现。画中少年红色裤管的黑色轮廓线,几乎完全承袭浮世绘的线条,巧妙地使人物从背景中凸显而出。
▲ 葛饰北斋
《富岳三十六景.神奈川冲浪里》是举世闻名的日本浮世绘作品,葛饰北斋以富士山为背景,描绘神奈川冲的巨浪翻捲着渔船,渔民们努力生存。套印使用了从欧洲进口的颜料「普鲁士蓝」。
▲ 歌川广重
歌川广重出自江户时代的最TOP艺术社团——歌川派。《名江户百景.龟户梅屋舖》放大局部枝干,将名胜风景龟户梅屋舖安排在远处,此构图手法深深征服了梵谷的心,他以油彩临摹了一幅《开花的梅树》(右图)。
▲ 文森 • 梵谷
浮世绘作为画中画,成为印象派画家笔下常见的创作元素,《唐吉老爹》即为代表。后印象派大师梵谷迷恋着浮世绘,他私藏超过600幅浮世绘,反复临摹。与胞弟通信来往中,梵谷无数次提及嚮往日本:「我全部的作品,在某种程度上,都奠基在日本艺术。」
日本与基督教的距离
这片基督徒人口仅占1%的土地上,日本与基督教的距离没你想像得那麽远。早在16世纪末,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开启了日本与基督信仰的第一次亲密接触。日本基督教并未局限于传统的布道模式,而是不断发展出多元且富有创意的福音策略,与日本平凡又温暖的日常融为一景。


❶ 神奈川县藤泽市
冲浪事工「Wave of Grace」
鹄沼海岸的铜像前,矢部先生搭起了一座小帐篷。每逢週一和週五,这座小帐篷便会如约出现,成为冲浪客的补给站。帐篷裡不仅提供饮料、充电器和冲浪板,更给矢部先生与冲浪客建立关係,甚至吸引了喜欢冲浪的牧者前来聚集交流。

❷ 无固定地点
东北亚基督教文学会议
日韩轮流主办的文学交流会议,旨在促进两国基督教文学研究者的互动,并从彼此的视角反思文学。儘管许多日本文豪如芥川龙之介、宫泽贤治等并非基督徒,但他们的作品字裡行间却蕴含了基督信仰的精神。透过文学研究,基督徒学者可以发掘福音与文学的连接点。

❸ 宫崎县仙台市
餐车事工「心之厨房」
「心之厨房」每週固定在两处营业,同时每月参与街友关怀事工,期盼透过料理与人连结。这是个刚刚起步的服事,愿宣教日引读者以祷告默默守护「心之厨房」。

❹ 宫崎县多贺城市
食物援助「生命之粮」
「生命之粮」主要事工为发放食物包,支援弱势群体的生活。他们定期去好市多领即期麵包,再由宣教士登门拜访,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。发放食物的同时,宣教士不只关怀人们的生活需要,更把握机会为他们祷告。

❺ 宫崎县仙台市
弱势群体生活支援
「Operation Blessing」国际福利团体与当地教会、差会携手合作,每月在勾当台公园举办关怀活动。他们不只发放「心之厨房」预备的便当和生活物资、献唱诗歌,也协助街友申请就业及租屋。这些陪伴不仅改善街友的生活处境,更让当地居民信任教会,为福音撒种鬆土。

❻ 茨城县利根町
基督祭典
日本人热爱祭典。然而,祭典往往涉及祭拜神明的宗教仪式,教会多半迴避。利根基督教会却另闢蹊径,举办「基督祭典」(キリ祭り),巧妙运用日本人熟悉的祭典形式,吸引许多路过的大人小孩走进教会,与会友和牧师自然交流,为教会与社区搭建福音桥梁。

❼ 茨城县利根町
舞蹈教室
只要把讲台遮起来,这裡就是舞蹈教室。由于亲戚拥有舞蹈专业背景,牧师灵机一动,想出了绝妙安排。日本人普遍对宗教存有戒心,灵活的空间运用,冲澹了宗教色彩,会友能以舞蹈教室的名义,邀请人来教会。

❽ 日本各处
语言学习
语言学习是宣教场上历久不衰的传福音策略。日本除了常见的英语教学,韩语教室也渐趋普及,这与众多韩国宣教士在此服事有关。另外,由于本土牧者不足,不少日本教会由韩国牧者牧养。

❾ 东京都东村山市
免费运动场
日本的免费运动场地少,这成为国际宣教会(One Mission Society)的宣教良机。他们将教会空地规画为运动场,开放给附近居民使用。由于场地毗邻神学院,成为会友、神学生与居民交流的绝佳场所。国际宣教会透过Line管理运动场,适时将福音活动讯息推播给常来运动的居民。

❿ 东京都新宿区
酒吧教会
除了婚礼,鲜少日本人愿意踏入教会。面对这样的现实,中村牧师走进酒吧,当起了调酒师。牧师每晚两次的短讲,成为这间酒吧的独特风景。在这裡,人们卸下厚重的面具,倾吐心裡话。虽然酒吧座位有限,却是一处温馨、敞开的地方。(见4月14日内文)

日本宣教史3个重要时期
Period 1
欧洲发现日本 1549~1612年
当马丁路德向罗马教廷提出改革诉求之际,天主教内部也掀起一股革新浪潮——以依纳爵和沙勿略为首的宗教领袖在法国创立了耶稣会,立志过着贫穷、贞洁的生活,并向外宣教。
这时适逢欧洲大航海时代,葡萄牙、西班牙的商船频繁往来东方。1540年,沙勿略把握时机,跟随商船,开启亚洲宣教旅程。他在旅程中偶遇一位日本武士,心裡萌生前往日本的想法。
1549年,沙勿略抵达日本鹿儿岛,在九州、山阴山阳、近畿等地展开传教活动。他是日本拓荒宣教先锋。此后,各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纷纷追随欧洲商队的脚步,来到这片福音贫瘠之地。
福音种子很快地在日本开花结果——数十位大名注受洗,近百万平民成为信徒,约占当时日本总人口4%。宣教如此成功,主要有两大关键因素:首先,欧洲商队带来了步枪、火药、织品等日本急需的物资;其次,传教士谨守清贫的生活作风,积极投入慈善工作,赢得地方大名的支持。
然而,福音盛况最终招致当权者的反感。1612年,德川幕府颁布禁教令,为这段宣教黄金时期画下句点。
注:日本战国时代的封建领主称呼。
Period 2
上帝VS.天皇 1873~1945年
明治政府成立之初,虽然延续了德川幕府的禁教政策,但在西方列强的施压下,不得不改弦易辙。1873年,日本废除禁教令,开始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思想与文化。而各大基督新教教派纷纷派遣具备医疗、教育等专业背景的宣教士前往日本,因此宣教成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。
基督教的发展没多久就遭遇严峻挑战。1890年,爱国主义思潮兴起,当局相继颁布了《大日本帝国宪法》、《教育敕语》、《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式规程》等法令,要求人们在学校喊天皇万岁、向《教育敕语》行礼,强化天皇的神性,剥夺人民的宗教自由。
面对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全球,日本政府为求自保,积极向外扩张,同时在国内肃清异己,禁止反战言论、逮捕外国宣教士,并强制组建日本基督教团,要求教会与政府合作。日本基督徒载浮载沉,教会活动日渐萧条,信徒人数锐减。
着名的日本基督徒知识分子
内村鑑三
在课堂上拒绝礼拜《教育敕语》,引起挞伐。
海老名弹正
曾用演说、布道,主张日本向外扩张是为义而战。
新岛襄、新岛八重
创立基督教同志社大学,在课程中带入基督信仰。夫妻两人都是日本重要的教育家。
Period 3
浇熄的火苗 1945年~
1945年日本战败后,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负责整顿百废待兴的日本社会。他修改宪法,保障人民的宗教自由,日本天皇也脱去神格。
由于麦克阿瑟的亲基督教政策,以及美国、加拿大宣教机构的援助行动,日本基督徒人数稳定增加。可惜这波宣教热潮以援助为前提,信仰根基未能扎稳在日本人的心土上。
1954年,美军的核爆实验导致日本渔船遭受辐射伤害,浇熄了这波宣教热潮。这起事件在日本社会掀起强烈的反美情绪,也间接影响民众对基督教的态度。自此之后,日本基督徒人数逐年下降。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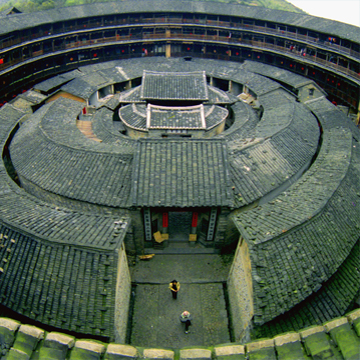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美国
美国